女性的憤怒,能為社會帶來革命性的改變嗎?
去年,美國經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性侵運動。這場反性侵運動從好萊塢起步,以燎原之勢蔓延到社會的各行各業。面對位高權重者的不合理要求,越來越多女性挺身而出。女性維護自身尊嚴的勇氣愈發受到鼓舞,要求平權的呼聲也越來越響。然而,女性的處境因此變得更好了嗎?我們該怎么理解這個時代女性的憤怒和發聲?我們可以從近期在海外引起熱議的圖書中管中窺豹,因為談論本身,也是一種反抗。
《成為》(Becoming)
作者:米歇爾•奧巴馬

《成為》是美國前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的自傳回憶錄。據BBC報道,在11月出版以來,僅用了15天,《成為》即打破了銷售紀錄,成為了2018年美國最暢銷的圖書。
在這本回憶錄中,米歇爾•奧巴馬回憶了她的成長經歷——從她在芝加哥南部度過的童年到她進入白宮的經歷。在其中,她描述了奧巴馬如何對她展開了追求,而她如何在一個夏天的晚上,愛上了巴拉克•奧巴馬,“當我允許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巴拉克身上的時候,”她寫道,“我的心怦怦直跳,那是一種混合著欲望、感激、滿足和新奇的感覺。”
米歇爾•奧巴馬在書中還首次指出,女性應該公開談論流產和不孕這些話題。因為她曾流產過,并因此很傷心,她不知道這類流產有多常見,所以她以前幾乎未跟別人提起這段經歷。在34歲時,她意識到“自己的卵子是有限的”。因此,她決定人工授精,并靠此生下瑪利亞和薩莎兩個女兒。
而當時,奧巴馬剛加入了州議會,工作非常忙碌,她只能自己處理人工授精的相關程序。在兩個女兒誕生之后,他們還必須艱難地平衡著忙碌的事業和當父母的壓力。這些生活上的困難使得她和巴拉克•奧巴馬的婚姻并不一帆風順。米歇爾•奧巴馬認為,婚姻咨詢曾挽救過他們的婚姻,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學著互相傾訴差異和分歧,并且求同存異的方式。
此外,米歇爾•奧巴馬還在書中,對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了批評。她寫道,特朗普是一個“厭女者”和一個“霸凌者”。她永遠也不會原諒特朗普,因為特朗普在競選的過程中,曾質疑奧巴馬并不是在美國出生的,因而不是一位合法的美國總統。這將她家庭的安全置于一個危險的境地。
阿夫華•希斯奇(Afua Hirsch)在《衛報》認為,對于女性主義者來說,“第一夫人”是一個很尷尬的概念。雖然這是一個涉及女性、地位很高的職位,但是由于這個職位要依附于丈夫的地位,所以第一夫人的“成功”一直令人質疑。
但是,米歇爾•奧巴馬的經歷很好地化解了這種尷尬——“她的生活就像一種煉金術”。她有著高尚的道德情操,還有勤奮努力的品格,不斷地以自己的方式為社會做貢獻。更重要的是,在種族主義思潮回潮的今天,她和奧巴馬已經成為了“美國夢”的一種代表性的敘述方式。她成為“第一夫人”,并不有損女性的尊嚴,反而成為了美國女性的“榜樣”。
《沒那么糟:強奸文化集》
(Not That Bad: Dispatches from Rape Culture)
編輯:羅珊恩•蓋伊(Roxane G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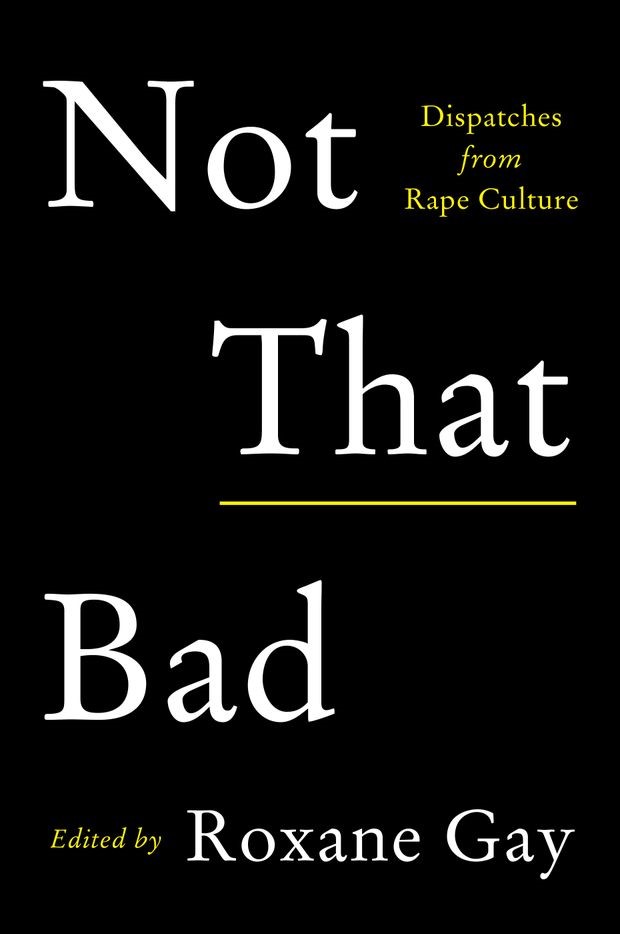
羅珊恩•蓋伊是美國著名的女性主義者和文化評論家。她曾寫過最受美國女性主義者們歡迎的幾本書,如《壞女性主義者》(Bad Feminist)和《饑餓:我身體的回憶錄》(Hunger:A Memoir of My Body)。《沒那么糟:強奸文化集》則是由她負責收集和整理,以第一人稱角度,記錄的有關于強奸、性侵和性騷擾經歷的文章合集。
據美國《娛樂周報》對她的專訪,她這項工作并不是受到“哈維•韋恩斯坦丑聞”的啟發而開啟的。在反性侵運動的前幾年,這個項目就已經預想好了。為什么要收集整理這些被性侵的經歷呢?她認為,很多女性都曾遭受過性侵犯,包括她自己,在12歲的時候曾被一群男孩在樹林里輪奸過。但是,社會上的輿論總跟她們說:“沒那么糟。”所以,她想告訴大家,這件事很可怕。她當時建立了一個電子郵箱,專門接收全美國各地遭受性侵犯經歷的文章。然后,她花了好幾個月,篩選整理出30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羅珊恩•蓋伊為這些陌生人的坦率和誠實所震驚。根據加拿大《環球郵報》報道,《沒那么糟:強奸文化集》中包括了好萊塢演員艾麗•西蒂(Ally Sheedy)在好萊塢的創傷經歷。她曾因為拒絕與導演或者制片發生性關系,而導致失去演出很多角色的機會。她也拒絕裸體出演或者演美化性侵婦女的電影,但是這也使得她的事業屢屢受挫。她還呼吁各位女性不要被外表欺騙,“要小心,有些男人會假裝成不是‘獵食者’一樣”。
除了艾麗•西蒂,其他大部分作者都是不知名的普通人。他們有年輕人與老年人、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甚至還包括男性。比如,一位名叫安東尼•弗萊(Anthony Frame)的專業滅蟲者,是該書中的兩位男性之一。弗萊描述了在他六年級時,他朋友的父親對他進行性侵犯。這使得他長大后,都不愿與妻子發生性關系。
“我希望人們通過閱讀這本書,能更深入地了解普遍存在的強奸文化,” 羅珊恩•蓋伊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希望它讓這個世界減少這種痛苦的經歷。”
《良善與瘋狂:女性的憤怒所帶來的革命性的力量》(Good and Mad:Revolutionary Power of Women’s Anger)
作者:麗貝卡•特雷斯特(Rebecca Trais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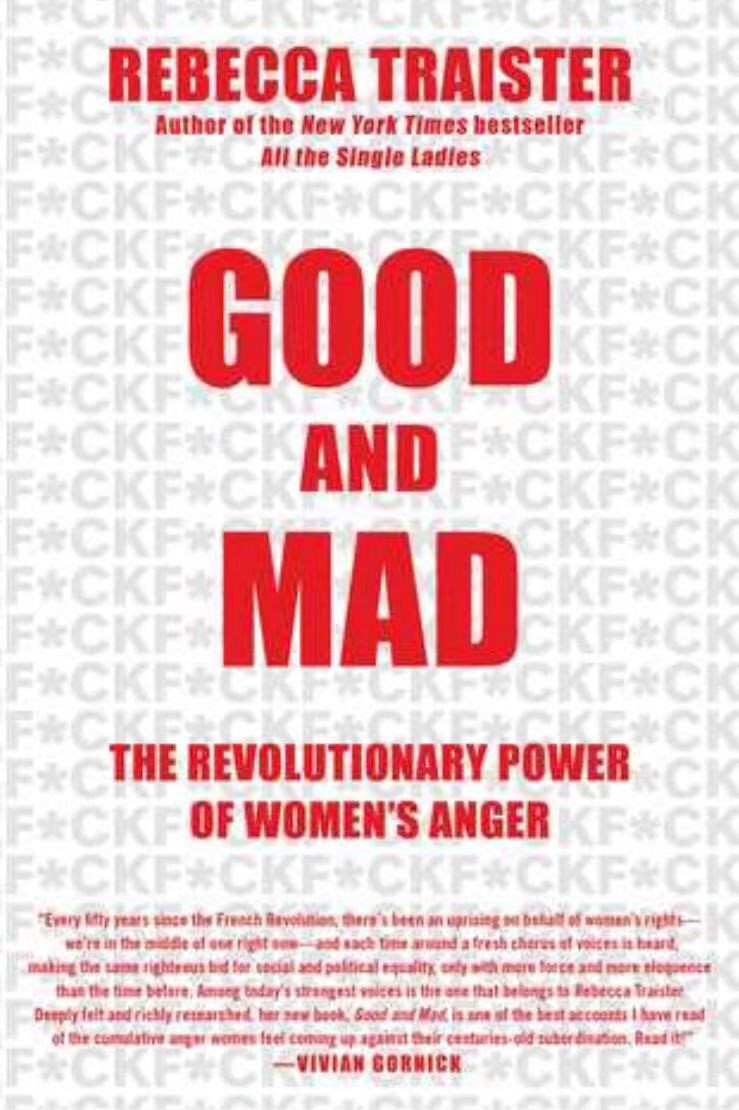
麗貝卡•特雷斯特是《沙龍》雜志政治和性別版塊的撰稿人。她曾寫過《我的孤單,我的自我:單身女性的時代》,并讓“單身女性時代”這個詞風行一時。而《良善與瘋狂》是她對女性的憤怒,在美國政治運動領域進行的研究和探索。
在2018年,女性的憤怒似乎成了美國輿論漩渦的中心之一。麗貝卡•特雷斯特認為,在2018年這些紛繁復雜的政治運動之前,女性的憤怒在政治上是存在著問題的。這是因為在政治上,美國的女性長期處于壓抑狀態。而這也堆積了許多憤懣和不滿。
麗貝卡•特雷斯特從女性爭取投票權運動開始,回溯了女性憤怒的歷史,她還分析了當時媒體和男性是如何看待這種憤怒的。她認為,女性集體的憤怒是政治變革的燃料,這種憤怒是一種“潛在革命時刻”,能夠推動改變政治權力分配,正如今天將會發生的那樣。而這種情況發生的主要障礙,是女性壓抑憤怒的習慣。因為人們經常會認為,憤怒的女性是不講道理的,非理性的和瘋狂的。“女性的憤怒激發了創造力,推動了政治和社會變革,而且始終如此。” 麗貝卡•特雷斯特總結道。
麗貝卡•特雷斯特認為,特朗普的上臺,也使得許多白人女性——她們從前奉行通過努力工作和變得美麗迷人的價值觀,來推翻刻板印象和性別歧視——也變得憤怒起來。雖然她們是這個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但是,特朗普的上任使得她們的憤怒被首次釋放出來。
這本書的觀點也引起了爭議。勞拉•基普尼斯(Laura Kipnis)在《大西洋月刊》中認為,女性的憤怒不僅僅指向男性,同時也會指向女性。尤其是在別的議題諸如種族、階級疊加進來的時候。比如,投票支持特朗普的白人女性,就被黑人女性所憤恨。那么,作為既得利益者的白人女性,是否會利用自己的權利只維護白人女性的利益,而不解決其他女性的不公正待遇呢?勞拉•基普尼斯認為,很明顯,有些人會,有些人不會,這具體要看其政治立場。麗貝卡•特雷斯特提出的解決方案——讓更多的女性擔任政治職務,雖然沒有錯,但勞拉•基普尼斯認為,她不相信政治智慧和價值觀會因女性的身份而自動獲得。這些女候選人在政治立場之間的不同,也會造成分裂。
伊蓮•布萊爾(Elaine Blair)則在《紐約時報》撰文認為,麗貝卡•特雷斯特所說的憤怒是當下美國的一種普遍情緒,它很難說是某種政治策略。憤怒的公民是否有敏銳的正義感?她們會不會變成暴徒?對待不同議題的憤怒值是不是截然不同的?這些問題在這本書里沒有提到,但也是非常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問題。
《合情理的憤怒:一個黑人女性主義者發現了她的超能力》(Eloquent Rage:A Black Feminist Discovers Her Superpower)
作者:布里特尼•庫珀(Brittney Coop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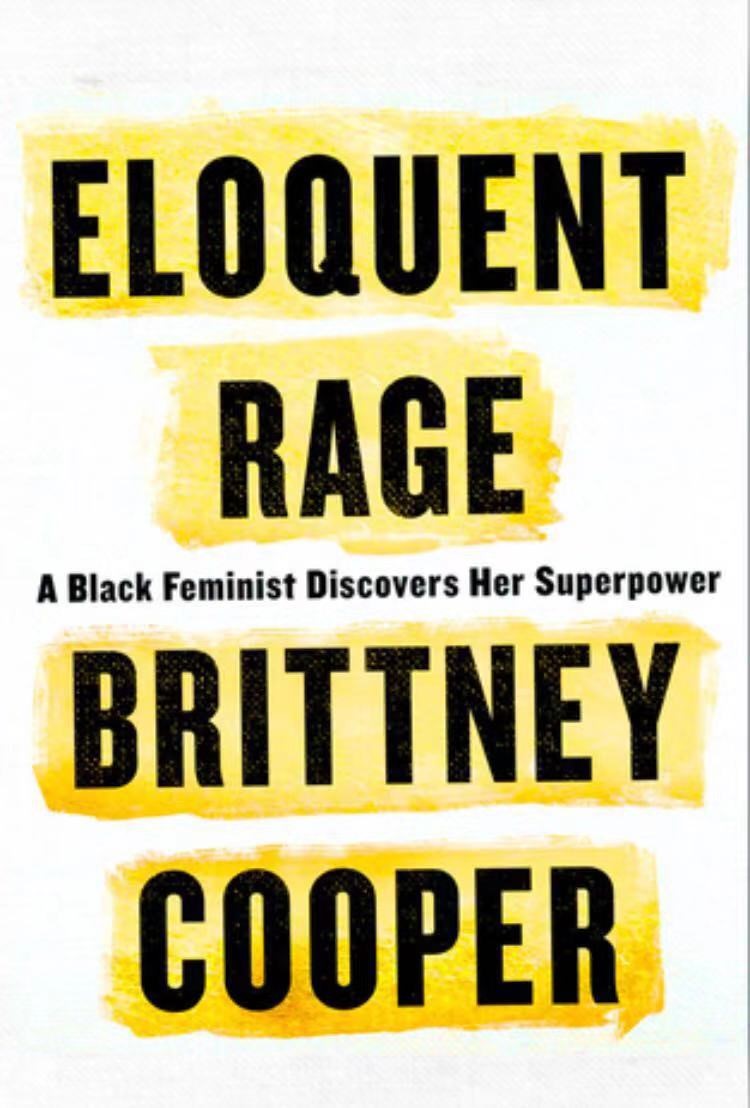
布里特尼•庫珀是美國羅格斯大學女性和性別研究系和非裔美國人研究系的副教授。她是一個黑人女性主義者,文化批評家和演說家。《合情理的憤怒:一個黑人女性主義者發現了她的超能力》是她的一本評論文章選集。她在一個日益倒行逆施的社會里,就黑人女性主義者所面臨的問題進行精辟的評論。
“我們黑人女性被告知是非理性的、瘋狂的、與社會脫節的和破壞性的。” 布里特尼•庫珀在書里寫道。她對此表示憤怒,并且認為這種憤怒非常合情合理。而且,她認為這種憤怒也是社會“進步和變革的強大能量來源”。
不同于很多評論以說理取勝,她在書里詳細描述了自己變成一名女性主義者的心路歷程,并在同時表達了政治上的分析。她與主流的女性主義者們很不一樣的是,她更強調她的黑人性。當然,她也并沒有無視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結盟的必要性。她在書中關切的問題是,黑人女性需要一個什么樣的世界?
布里特尼•庫珀之所以強調黑人性,是因為她很清楚白人女性主義的局限性。她認為,白人女性主義的目的是與白人男性平起平坐。對黑人來說也是如此。黑人男性爭取的自由就是想要和白人男性平起平坐。但是,黑人女性是布里特尼•庫珀能看到的唯一的沒有性別特權,也沒有種族特權的人群。她還認為,在絕大多數白人女性眼里,白人的身份,其實比性別更重要。
她認為,像網球明星塞雷娜•威廉姆斯,前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和歌手碧昂絲都是當代黑人女性主義者的榜樣。她們在不公的社會里,通過自己努力,在她們的領域中成為佼佼者,贏得了大家的尊重,并改變了“游戲規則”。這超越了種族和性別。所以她認為,我們不僅只是要改善黑人女性,而且還要改善整個社會。“我從跟本上認識到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的女性主義不一樣,”但是布里特尼•庫珀“并不討厭白人女性主義者”。
賽達•格蘭迪(Saida Grundy)認為,“個人的就是政治的”已經成為了女性主義者的常識。我們的情緒并不算是宏觀政治領域的一部分。而我們的欲望、不安全感和自我認同才是政治表現形式的一部分。但是,布里特尼•庫珀這本書則相反,她把憤怒提到了一個很高的位置。而且,她用非常個人化的手法,從她自己的生活經歷入手,圍繞著她復雜的童年,虐待狂的父親和母親的謀殺等個人敘述,來描繪一個黑人女性主義者與白人女性主義者的不同之處。
因此,她談論了許多黑人女性間的友誼,并強調黑人性本身。賽達•格蘭迪認為,她對碧昂絲的崇拜也不僅僅是因為她是女性主義者。現在許多美國名人都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這已經變成了一種讓自己更流行的營銷方式。不管是泰勒•斯威夫特,還是凱蒂• 佩里,甚至連伊萬卡•特朗普都稱自己某種女性主義者。但是對于布里特尼•庫珀來說,碧昂絲之所以是女性主義者,并不是為了她自己的名聲,而是因為布里特尼•庫珀理解和懂得一個黑人女孩成長的痛苦,而這種經驗,是白人體會不到的。
標簽: 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