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秋節(jié)“天降大瓜”的吳秀波人設(shè)崩塌、出軌事件,在上周有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進展。曝與吳秀波婚外情7年的陳昱霖被吳秀波指控敲詐勒索,于11月5日被警方帶走。而陳昱霖父母稱這一切都是吳秀波的圈套。
周一商量選題時,跟編輯提及周末有一熱點仍在討論之中:吳秀波事件與“大房教”。編輯的回答讓人忍不住為他單純的腦回路鼓掌:“大房教?是說相親要有大房子嗎?”
“大房”當然不是“大房子”的意思,而是“正室”“正妻”之意,“大房教”信徒指的是那些站在正妻立場攻擊第三者的人們。網(wǎng)絡(luò)造詞之風將這一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再次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此番討論始于吳秀波事件,因編劇六六的發(fā)聲而“燎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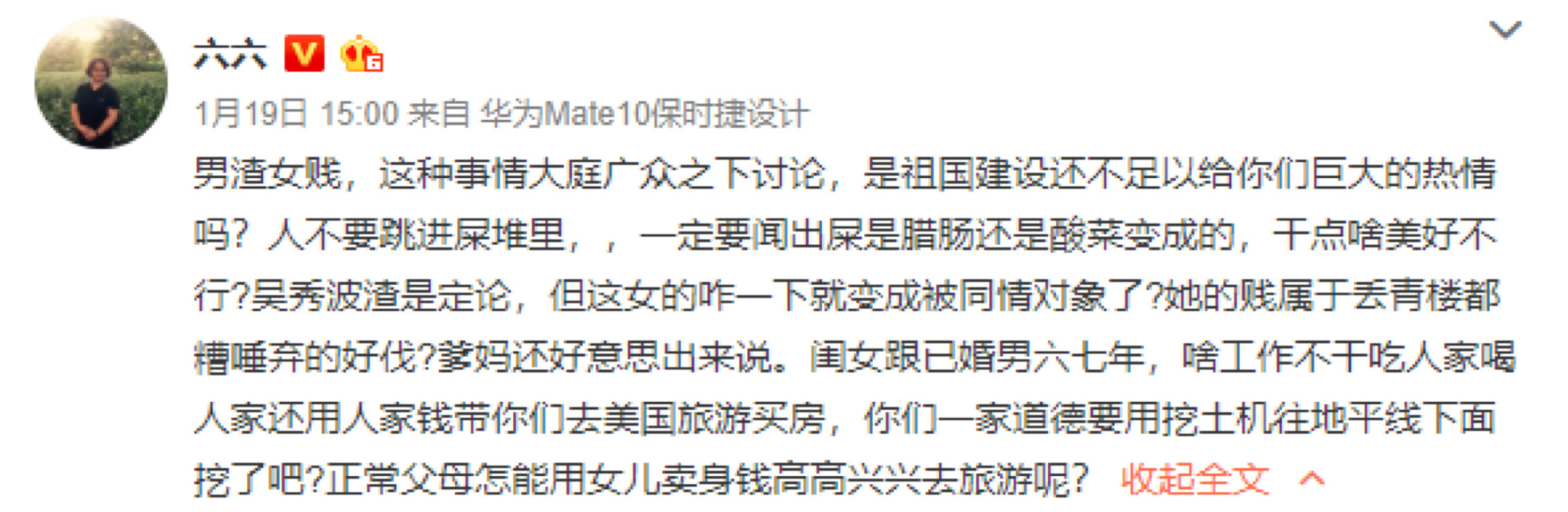
截圖來自六六的微博。
六六在這條微博之下回復網(wǎng)友評論道:“倆人今天下場就是活該……”“那時候三觀不清,現(xiàn)在來裝可憐。他閨女傷害人家正室這事,就算過去了是吧?”此后,六六還撰文談及“大奶”和“小三”的區(qū)別,簡單來說就是正妻真心為丈夫,第三者為錢。
“大房教”言論在中國當代婚姻輿論場中相當常見——“小三”作惡,有任何惡果皆為自作自受;“正室”利益不可侵犯,打“小三”具有天生的正當性。在吳秀波事件中甚至上演到無視法理的程度。而這套流行話語體系所隱含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更是令人心寒,令人不禁想發(fā)問,為何到今天,還會有女性以“正室”身份為尊?
“大房”
古代婚姻家庭制度的殘留物
雖然一夫一妻制已經(jīng)施行多年,“正室”“大房”的提法依然普遍存在。話語即權(quán)力,“大房”話語背后的權(quán)力分配,與醞釀該詞的中國古代婚姻家庭制度有無法割裂的關(guān)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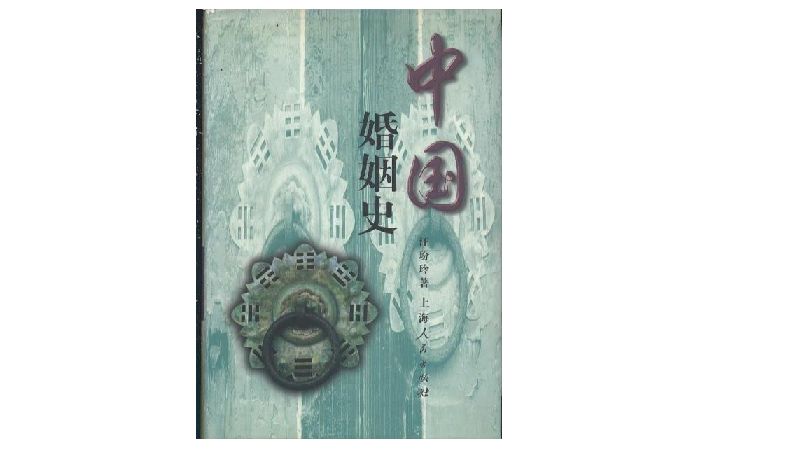
《中國婚姻史》,作者: 汪玢玲,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1月
據(jù)汪玢玲《中國婚姻史》考證,中國母系社會時代主要的婚姻形式為“雜婚”和“血緣婚”。“雜婚”是最原始的婚姻形式,即無視血緣關(guān)系隨意發(fā)生性關(guān)系;“血緣婚”指同輩兄弟姐妹之間可以結(jié)婚,隔代之間不可,在“血緣婚”制度下,男男女女都過著“多夫多妻”的生活。

兩種婚姻形式都可以從神話傳說中找到蹤跡,“感天受孕”體現(xiàn)雜婚制度;伏羲女媧兄妹結(jié)合,體現(xiàn)血緣婚制度。上圖為伏羲女媧圖,蛇尾象征交媾。女媧手執(zhí)用于研究天象歷法的“規(guī)”,一種說法稱早期歷法設(shè)立與女性經(jīng)期有關(guān);伏羲手執(zhí)用于丈量土地的“尺”。
母系社會逐漸向父系社會過渡時期,出現(xiàn)了一妻多夫、一夫多妻的婚姻形態(tài),即“多偶制”。此時普遍存在兄弟共妻、姐妹共夫的情況。慢慢地人們發(fā)現(xiàn)氏族內(nèi)長期通婚,生下的后代不夠健康,所以男子需要到其他氏族獲得妻子,獲得的方式為“搶”或者“買”。這樣得到的妻子,通常只有一位,故出現(xiàn)了一夫一妻的“對偶制”。“對偶制”的一夫一妻,全然無當代婚姻的半分平等。女子是父母的財產(chǎn),被“買走”或者“搶走”之后,是丈夫的財產(chǎn)。
據(jù)汪玢玲的婚姻史研究,父權(quán)制萌芽與對偶制幾乎同時產(chǎn)生,丈夫擁有財富,需要有明確的繼承者,因此妻子要嚴守貞操。丈夫的地位被無限推崇,如《儀禮》所言:“夫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為了承認丈夫的地位,還存在過一種叫“產(chǎn)翁制”的民俗,即女子生產(chǎn)后會被趕下床鋪干活兒,丈夫躺在嬰兒身邊裝孕婦接受鄰里道賀。

美劇《使女的故事》中,作為繁衍工具的使女生產(chǎn)時,主人家的妻子會同時假裝生產(chǎn)。這種生產(chǎn)儀式與產(chǎn)翁制異曲同工。
在奴隸社會階段(夏商時期),一夫多妻是少數(shù)奴隸主的特權(quán)。此時母系社會的影子還沒有完全消除,商朝的部分婦女仍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如女軍事家婦好。但到了周朝宗法制建立之后,女性徹底失去了母系社會時擁有的地位。宗法制下的婚姻為了穩(wěn)定財產(chǎn)繼承制度,開始劃分妻妾,只有正妻嫡子有繼承權(quán),妾的地位如同奴仆,家庭等級秩序就此形成。對女子貞操的要求也逐漸確立。
后來封建社會的婚俗無論如何演變,女性附屬于男性的地位、妻妾地位差距幾乎沒有改變過。古時如果丈夫無視妻妾的秩序,還會觸犯法律。如《漢九律》規(guī)定“亂妻妾位”屬于犯罪,清朝法律規(guī)定“凡以妻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
那么“大房”“二房”的劃分是從何而來的呢?這與古代建筑格局有關(guān)。“大房”為正妻所居,多在宅邸東側(cè)。“二房”“三房”即為妾,但封建時期法律會限制男子納妾數(shù)量,如《紅樓夢》中的賈政按地位只能納兩個妾,這樣一來妾室也有了地位高低之分。“二房”可以和“大房姐妹相稱,地位略低于正妻,如嫁給賈璉的尤二姐;姨娘地位要差得多,如趙姨娘;通房丫頭則連妾的名分都沒有。
由此可見,“大房”“正室”等詞誕生的歷史背景賦予了它尊貴的含義,在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之下,“大房”意味著正統(tǒng),意味著掌管妾室和家務(wù)的權(quán)力。“大房”同時也是家庭穩(wěn)定的維護者,是秩序的象征,這些又反過來加強了“大房”地位的合法性。
“小三”與“渣男”
現(xiàn)代婚姻制度失敗的產(chǎn)物?

《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2018)劇照。
在近期熱播的電視劇《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中,揚州通判盛纮在家“寵妾滅妻”,讓妾室掌握管家大權(quán),這在封建社會發(fā)生的可能性很低。在古代社會背景之下,是不存在“小三”和“渣男”一說的,有的男子雖然在外養(yǎng)“外室”(與男子同居但無任何名分的女子),會被家族認定為奇恥大辱,但“外室”的地位比“妾”還要更低微,不足以與“妻”抗衡,“妻”也沒有資格問責丈夫“渣”。
所謂的“第三者”,是現(xiàn)代一夫一妻制的產(chǎn)物。而一般認為,受文化影響,男性出軌的概率要高于女性,“小三”和“渣男”的說法應運而生。五四運動之后,全國上下提倡婦女解放、自由戀愛,沖破傳統(tǒng)禮法的西式婚姻締結(jié)制度讓某些遺老們氣得直道“人心不古”。但當時以愛情價值為先的戀愛觀,隨著社會的發(fā)展還是回歸到“門當戶對”的婚姻之中,我們需要無奈地承認,家庭依然是生產(chǎn)功能為先,情感價值隨后。現(xiàn)代一夫一妻制一方面提升了女性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因為更為自由的制度,為婚姻的不穩(wěn)定性埋下了種子。
如果封建遺老能活到今天,也許會氣得吹胡子瞪眼,禮教森嚴的時代,“外室”怎么可能與妻子一爭高低,甚至趕走妻子取而代之?而現(xiàn)代婚姻制度下一切都成為了可能,“外室”擁有了新的名字,好聽點的叫“情人”,中規(guī)中矩的叫“第三者”,難聽點的叫“小三”“二奶”。
一種流行觀點認為,“第三者”是現(xiàn)代婚姻制度失敗的產(chǎn)物。記得大學時上小說鑒賞課,老師說你們都還年輕,所以對忠貞的愛情還抱有幻想,然而人到中年,出軌是一種很正常的欲望。她舉了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帶小狗的女人》為例,兩個普通人發(fā)生了婚外情,與虛偽的社會相比他們的感情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二人頭一次體會到“愛”的滋味,同時也為此苦惱——
他們覺得他們的遇合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他們不懂為什么他已經(jīng)娶了妻子,她也已經(jīng)嫁了丈夫……他們商量了很久,講到應該怎樣做才能擺脫這種必須躲藏、欺騙、分居兩地、很久不能見面的處境。應該怎樣做才能從這種不堪忍受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呢?
“應該怎樣做?應該怎樣做呢?”他問,抱住頭。“應該怎樣做呢?”

《情婦:關(guān)于女性第三者的歷史、神話與釋義》,作者: 維多利亞·格麗芬,譯者: 張玞,版本: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2002年1月1日
“第三者”是現(xiàn)代婚姻制度的犧牲品,外遇的出現(xiàn)是因為婚姻中出現(xiàn)了問題——缺乏交流、持續(xù)爭吵,而情人(且多為情婦)成為了“替罪羊”。這是維多利亞·格麗芬在《情婦:關(guān)于女性第三者的歷史、神話與釋義》中引述的觀點。在前幾年大火的日劇《晝顏》中,我們也能看到此類觀點的痕跡。家庭主婦笹本紗和與生物教師北野裕一郎陷入婚外戀中,二人的婚姻均出現(xiàn)了問題,后來女方成功離婚,男方因為妻子過于強勢無法離婚……當年追劇時在網(wǎng)上經(jīng)常能看到類似的留言:“三觀被刷新了……”“為什么我會被婚外情打動……”

日劇《晝顏》中上戶彩飾演的笹本紗和與齋藤工飾演的北野裕一郎。
然而“第三者原罪論”支持者在此堅持捍衛(wèi)婚姻的穩(wěn)定性,認為《晝顏》之類的作品美化婚外情、用“真愛”為偷情洗白。他們厭惡這種真愛至上不顧家庭倫理的價值輸出,厭惡打著純愛的幌子來掩飾內(nèi)心的怯懦。每個角色都沒有擔當,既沒有勇氣徹底離婚與愛人在一起,也沒有足夠的責任感維持家庭關(guān)系、對伴侶負責。
從中不難看出一夫一妻制婚姻中存在的情感自由與穩(wěn)定性之間的矛盾,當出現(xiàn)問題之時,是選擇自我還是選擇責任。所以與其說“第三者”是現(xiàn)代婚姻制度“失敗”的產(chǎn)物,不如說它是自由婚姻制度“不穩(wěn)定性”的見證者。
而婚姻不穩(wěn)定的原因有很多,除了上文提及對“愛”的需求之外,還有很多原因與“利益”二字捆綁。后者也是很多影視劇著重呈現(xiàn)的對象,如今天成為網(wǎng)絡(luò)表情包素材庫的《回家的誘惑》。

《回家的誘惑》(2011)劇照。男主洪世賢被戲稱“史上活得最清新的渣男”。
“大房”打“小三”
以“正室”為尊的心態(tài)背后,藏著什么?
在“大房教”話語體系下,兩種婚姻體制的產(chǎn)物發(fā)生了正面沖擊:“大房”作為傳統(tǒng)秩序的代表和家庭穩(wěn)定的象征,對自由婚姻制度下誕生的不穩(wěn)定因素代表“第三者”發(fā)起攻擊。這場攻擊也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婚姻體制內(nèi),自由與穩(wěn)定性的矛盾之所在。
它表面上維護的是現(xiàn)代婚姻平等的一夫一妻制,維護妻子的正當權(quán)利,但這恰恰是妻子與丈夫地位不平等的體現(xiàn)。
如果夫妻雙方地位是平等的,那作為破壞婚姻契約的過錯方,丈夫才該是直接責任人,妻子應該向丈夫追責,而不是“喊打小三”。而以“正室”自居、為不擇手段打“小三”賦予正當性的話語背后,是妻子將自己的身份價值依附于男性的結(jié)果——守住“正宮”之位,守住賦予自己“正宮”地位的丈夫,是妻子的“天職”;丈夫再“渣”只能在家里收拾,不能離婚便宜“小三”……
以“正室”身份為尊,對“小三”窮追猛打,“大房教”式女權(quán)所維護的女性權(quán)利,本質(zhì)上是男性所賦予的。就像甄嬛走向高位利用的是皇帝的權(quán)勢;《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中的庶女費盡心思嫁入豪門,成為伯爵府嫡子正妻,所獲得的地位是丈夫給予的……在這些劇目中,女性之間爭勇斗狠,萬般算計。如果說宮斗劇、宅斗劇是受歷史限制,展現(xiàn)男尊女卑社會之下女性的無可奈何;那在早已實現(xiàn)一夫一妻制的現(xiàn)代社會仍然上演“宮斗”“宅斗”戲碼,以獲得最終勝利、守住丈夫為榮,是否意味著有很多人的精神與思想,還殘存于古代?
當婚姻出現(xiàn)問題時,“大房教”信徒所反思的不是感情本身,而是將矛頭指向“第三者”,以維護婚姻的穩(wěn)定。這種穩(wěn)定是一種虛偽的穩(wěn)定,貌合神離的穩(wěn)定,并且是以犧牲個人生活質(zhì)量為代價的。這在現(xiàn)實中有太多例子了,如“且行且珍惜”夫婦。
與對“小三”態(tài)度相對應的,是社會對“大房”的要求。“大房”要有“大房”的范兒,要鎮(zhèn)得住家,退得了小三,守得住丈夫,在丈夫出事的時候要維護夫妻二人的體面和尊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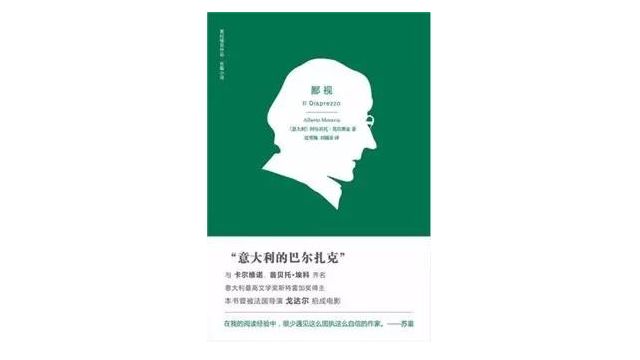
《鄙視》作者:(意)阿爾貝托·莫拉維亞,譯者:沈萼梅、劉錫榮,版本:譯林出版社2014年2月
也許“大房教”的存在,正印證了婚姻制度與社會經(jīng)濟制度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女性將自己困于婚姻之中,通過打“小三”泄憤,卻不與出軌男性正面相抗,不直面自己的感情困境,實在是有太多無奈——維持家庭穩(wěn)定和養(yǎng)育下一代的責任壓在肩頭,如何能隨自己的意愿,說離就離呢?只能退而求其次,打退小三,穩(wěn)定婚姻。
可是當代女性,真的沒有別的選擇了嗎?
在英劇《福斯特醫(yī)生》中,發(fā)現(xiàn)丈夫出軌的女主角也經(jīng)歷了一番“惡戰(zhàn)”,她收集證據(jù)、分割財產(chǎn)、在第三者的父母面前揭露一切。在第一季的最后場景中,女主角看著前夫與他的新婚妻子,露出了釋然的微笑;廣場上有人突發(fā)疾病,身為醫(yī)生的女主角緊忙前去救治……結(jié)尾一系列慢鏡頭不如很多電視劇“爽”,但它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女性面對出軌的一種積極的解決思路——女性的價值從來不是被男性所定義的,可以從職業(yè)中獲得;婚姻的目的不是留住丈夫和維持穩(wěn)定。
而對于那些傷害你的人,窮追猛打何嘗不是對自己的二次傷害?就像電影《消失的愛人》中,女主為懲罰出軌的男主自導自演了一場綁架案,最后將丈夫留在了身邊,卻永遠過起了人前恩愛、私下兩相無言的生活。

美劇《消失的愛人》(Gone Girl2014)劇照。國內(nèi)曾出版原著中譯本《消失的愛人》(譯者:胡緋;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3年6月)。
標簽: 大房教